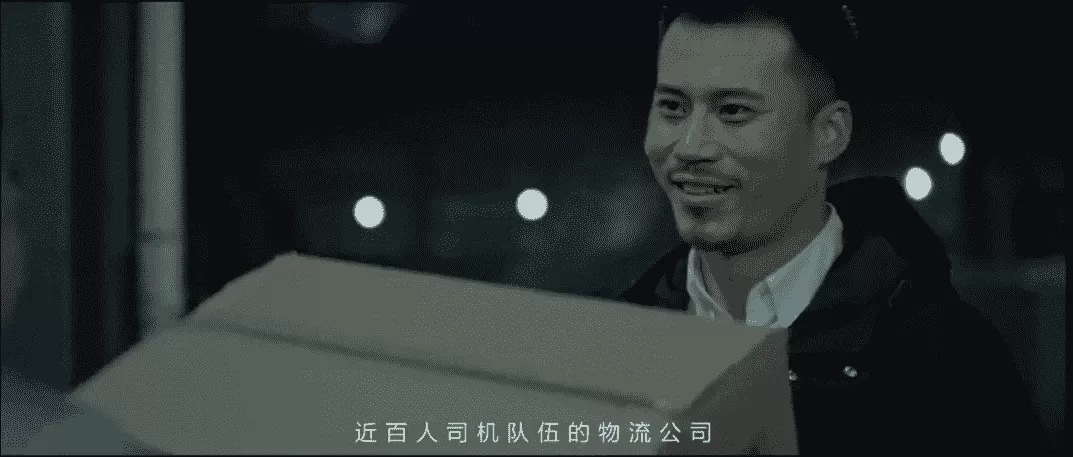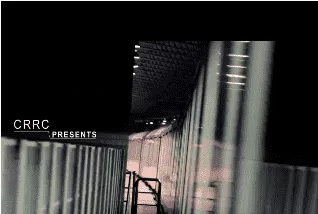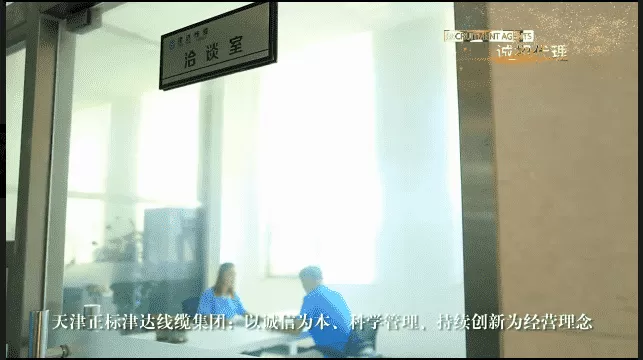玉林纪录片拍摄地
什么时候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1938年 夏天,徐肖冰第一次拍摄毛泽东照片。下半年,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如何拍摄一部纪录片?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片子不是要求很高的大制作,有几点可以参考:拍摄周期因制作题材的不同而不同,国外和大电视台的大的制作会很长(几年或十几年),小的(几个月-1年不等)。不论怎样,拍摄的前期准备工作(选题、考察、文案等)要占整个工作的 50%--80%不同(时间和精力投入)。1. 题材: 选题很重要,你要反映描写的是什么?2. 实地拍摄前采访(采风):确定选题后,条件允许的话,带上台小DV机,去实地采访、考察、核实题材。并拍些基本情况回来,作参考。3. 细化题材(文案工作、更具体了):将考察的实地情况和现有资料结合,作精细的案头工作--拍摄前的内容准备工作。4. 确定拍摄:按最初的方案去实地拍摄。
纪录片龙脊
这部作品以广西龙脊山区人民为创作原型,用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描绘一个恒久的中国村落里的一群的百姓形象。由于作品集中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运、以及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因而产生了丰富多义的社会意蕴。作品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观照淳朴、本色、生生不已的龙脊山人。
龙脊山区具有中国内陆地区的原生自然面貌,龙脊山区人民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和思想情感既具备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又鲜明朴素地体现着中国百姓的乡村生活,体现着中国人代代相承的成长、变化、奋斗的生命本质意义。他们很普通很平凡,但他们的朴实和坚韧的品格,却像龙脊山区的山脉一样给人以坚实的力量感。透过这里的社会生活现状,我们体察到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是怎样用自己勤奋的劳动创造着生活。作品发掘他们恒久不变地热爱生活、勇敢面对艰辛的情感;发掘他们乐观向上的积极的生命意识。
纪录片《龙脊》的主题立意便建构在对龙脊山区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和龙脊人不变的精神品格这种变与不变的关注和思考上。力图通过对龙脊人生产、生活及情感活动的细腻纪录,阐释对普通人的关切,阐释对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组织的思索,阐释人与家园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艺术与生活也在片中形象地产生联系,由此激发人们思想火花的碰撞与情感的升华。
本片以潘能高一家为贯穿线索,展开这个村庄的故事。创作者把镜头对准这一家人,以静观的方式记录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此力求浓缩出当今农村社会。此外还关注了另外一个人物——潘军权,通过他的活动来反映农村里另一些人要求改变的愿望。以潘能高和潘军权两条线索交织结构的构成样式,是本片区别于通常的以“三一律”(一条主线、一位人物、一个故事)为结构样式的纪录片的最大特点。这是一种“复调式”的表现样式。通过这两种人的行为和方式,让我们多角度、多时空、立体地透视龙脊山,龙脊人。
拆开纪录片,所见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的镜头。没有镜头,就没有影视片的结构元素,更谈不上句子、片断和成片。剪辑,就是剪裁和组接素材镜头,从而表达中心思想。按照生活逻辑剪辑,是纪录片的表面追求。表达中心思想,才是纪录片的根本愿望。
生活逻辑,主要指客观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素材镜头虽然取自生活时空,但它一旦离开生活时空,就随即变成了假定的时空。坐在剪辑机前,就是要把这些假定符号,剪辑得像真实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要模拟得可以乱真。写人物,好像人物真的在观众面前活动;说事件,仿佛事件活灵活现地就在观众面前展示。谈景谈物也都如此。只有这样,观众才可以在不经意中接受中心思想,而尽可能少地参进他们自己的思想、修改编者的用心。如果剪辑得不像真的时空,不仅中心思想传递不出去,反倒任何观众都会毫不客气地举起手中的遥控器,把片子毙掉。制定叙事的引导因素,建立全片的结构支点,是剪辑纪录片的关键。纪录片不像剧性片那样处处虚构,也不如小说创作动不动就可以纵横驰骋。时间对于纪录片摄制者似乎是最不公平的。许多事过去了就过去了,等到赶去,正在进行时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有时候,即令身处事件的现场,扛着摄像机面对错综复杂的信息对象,也最多只能立足一个视点,抓到一个侧面,无可奈何地让更多的信息溜走。可见,素材镜头向来满足不了编辑的愿望,而编辑却要不断满足观众的需求。《龙脊》倘若没有对路的引导因素和强有力的结构支点,去分段结集最有表现力的意义镜头,删除无用或可用可不用的镜头以及替补差缺的镜头,就很难把握住人物的脉搏,什么生活逻辑、什么中心思想,一切都等于零。在这部纪录片片里,摄制者设立了新学期开学,考试,淘金,满月酒等画面,分别成为几个部分的核心表述,同时配上其他的段落镜头,犹如无形的支柱,撑起了《龙脊》一片中最有代表意义的几个阶段。
摄制者与叙事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摄制者指的是负责拍摄和制作的工作人员,叙事者则是剪辑台上假定的陈述行为主体,他与视角一起构成叙事。有时他在片中做些串场、主持、佐证和铺垫性工作,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隐身幕后,或主观或客观地讲述故事。根据镜头和解说词分析,叙事者一直跟在村里的人们身边,他的视线始终伴随着潘能高,有时还发出一些议论,这就是文学界常说的第三人称主观叙事模式。片中的叙事者虽没有以“我”自称,但时时处处他都以“我”存在。比如他和潘军权一道从淘金所在地一路回家的一段,潘军权小心翼翼地怀抱着辛苦淘来的金粒回家,一路上,步履轻快,回到家以后,把金子给邻家女孩看似的喜悦自豪,足以见藏在镜头后的叙事者的踪影。叙事者是一种添加因素。生活中的事,无人称也无角度,在客观时空自成叙述状。纪录片却必须有叙事者,没有叙事者就无所谓叙事。既然有叙事者,就必定有叙述人称,有叙述人称就必定有人称视角。从哪一角度观察,从哪一角度立题,从哪一角度取材,最后从哪一角度剪辑,一环套一环,层层渐进。
纪录片一词最早源于电影。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是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纪录片运用电影电视的先进手法,以摄影或摄像为手段,对事实作比较系统、完整的纪录报道,它要求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拍摄真人真事,最大限度地排斥虚构与扮演。
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录片的根本与生命所在,是纪录片与生俱来的本性。“物质复原的现实”一直是纪录片创作的原则与理论依据。它强调表现上的客观化,强调社会生活的客观记录,强调对生活原始形态的尊重,强调再现生活的具体情境。可以肯定地说,离开真实/客观,纪录片将不复存在。然而,可以肯定的说,纪录片决不是绝对真实/纯客观的展示。
第一,纪录片作为一种创作行为,绝对真实/纯客观展示是不可能存在的。纯客观展示只是纪录片对于真实的永远的、渐近的追求,创作者以他们的真诚无限地接近真实。因为有了真诚,有些事可以经过记者的请求或安排拍摄下来,而不仅仅是记者旁观的冷静的记录;同时也因为这种真诚,纪录片在取得观众认同的基础上,也可以出现一些心理意象,以此延伸纪录片在客观之后的意味。
第二,如果说创作者不追求作品的终极意义,只是希望通过被拍摄对象,或拍摄者自身行为过程所体现的一些信息,来反映事物的存在状态,那是创作者的无知和软弱。约翰·格里尔逊在对纪录片进行定义时指出,纪录片就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纪录片就是从日常生活中拍出一部戏剧来,从一个问题中写出一首诗来”,这里的创造性处理,戏剧与诗更多地都包含有创作者的情感与意图,这些都表明,一部真正的纪录片是一部主题与形式有机结合的整体,是基于创作者对观众与客观事实的尊重,是一部用真实材料写成的“故事”。
《龙脊》的风格是客观纪实的。全片基本保持客观纪实的特点,解说词追求平实的风格,尽量少用或不用,片中以大量真实、自然、生动的生活情景的记录,带给人们身临其境的感受;在音乐的运用和某些情节的处理上,却又体现了一种主观的表现色彩,比如,潘能高班里的同学就常喊:“潘能高,真能干。”他爷爷常常到教室门口偷偷地看孩子念书。插秧时,爷爷突然说了一句:“潘能高,真能干。”这实际上是个完整生活的段落,正巧与前面呼应,而且完全没有设计,但比设计的要巧妙的多;还有其中多次出现的山歌村调,可以看成一个音乐引导式,让它为纪录片唱起主调,这种巧妙的音响安排,使纪录片捕捉到了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让全片富有人情味,并折射出一种情感,传递某种心灵语言和观念形态。这种主观性和纪录片的内核——客观性一起支撑纪录片的创作。
在纪录片领域,文化人类学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国际通用"货币",是纪录片中的一个大项。它被比较多地运用于一个足以产生审美距离的异质文化的考察,因为我们本身所拥有的文化视野与之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容易发掘对象身上的价值意义,观察者的视角容易找,观察者的位置容易显现出来。对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也不是不可以有用武之地,但是因为它离我们太近,近得包围了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我们的视角容易被局部的精细描述所限定,宏观上的把握不容易达到。这正是观察者的角度所带给我们的局限。要超越这种局限,就要使自己站在尽可能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
总体上说,《龙脊》是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幅乡村生活的图景,在个别地方,着以淡彩渲染,此为一种尝试,以求新意。《龙脊》的意义不在于缅怀过去,它关注的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生活现象,注重生活的厚重和内涵的丰富,追求并保持在真实自然的氛围中流露思想情绪。
1408幻影凶间这部影片的拍摄背景
【史蒂芬·金制造】
在瑞典老家拍摄了多部作品,其中还有一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使得编导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在家乡电影界的地位无人能及。而美国的观众和评论界注意到这位天才电影人,还是通过他于2005年在好莱坞执导的那部惊悚片《绝地威龙》--克里夫·欧文和詹妮弗·安妮斯顿分别在影片中饰演两个对婚姻不忠的公司高级主管。而他的最新作品《1408幻影凶间》则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同名惊悚短篇故事,可以说,这部影片将哈佛斯特朗姆带至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类型片领域中,而故事所处的世界,则是由毋庸置疑的恐怖大师所创造的。也许史蒂芬·金这个名字会让很多年轻的电影人望而却步,更何况是初来乍到的哈佛斯特朗姆,不过作为他的第二部英语作品,哈佛斯特朗姆还是有十足的信心拍好的。
相信最让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高兴的是,大部分曾为《绝地威龙》立下汗马功劳的幕后功臣也皆数回归,包括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剪辑师彼得·伯耶尔(Peter Boyle)、服装设计师纳塔利·沃尔德(Natalie Ward)、美工师安德鲁·劳斯(Andrew Laws)以及摄影师比诺伊特·戴尔霍米(Benoît Delhomme)--在哈佛斯特朗姆的眼中,这是一个最有创造力的幕后团队,更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出色的剧本为影片做保障,一个短篇故事到了创作过大量恐怖作品的马特·格林伯格(Matt Greenberg)和曾获得金球奖的编剧二人组拉里·卡拉斯泽基(Larry Karaszewski)与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手中后,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电影剧本。
除了剧本,演员阵容的配备也着实令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眼前一亮,影片中那个饱受折磨的作家迈克·安瑟林的扮演者是约翰·库萨克,好莱坞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库萨克表示,在答应接拍影片之前,他就早已经看过了那部由哈佛斯特朗姆执导、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邪恶》(Ondskan):“这部影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在想,创造它的人,一定是一位电影天才。没想到,我竟然有幸和这位天才合作。”
另外,约翰·库萨克还表示,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特殊的地域限制,也是保证这部影片的因素之一:“他来自瑞典,瑞典人不但非常出色,还对未来拥有神奇的预见能力……他们总是非常干脆地接受这些灵感,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看成是命运的象征。” 哈佛斯特朗姆则认为能够让库萨克来饰演迈克,是他的幸运:“我丝毫不会怀疑他的表演能力,但同时他身上还具备一种招人喜欢的温暖气息。男人喜欢他,女人爱他--我希望他能够将这种特质带到影片中来。”
约翰·库萨克身上确实有那种能够让观众喜欢上自己的能力,而这也就成了像《1408幻影凶间》这种叙述性的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认为:“只有迈克·安瑟林的魅力足够大,才能吸引住观看影片的人,让观众不仅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还能明白在生活中,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继而喜欢上他。”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库萨克阅读了影片的灵感之源--史蒂芬·金的原著短篇故事,它最初只是一本音频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后来收录到了于2002年出版发行的短篇故事集《世事无常》(Everything"s Eventual)中。看完之后,库萨克吓出了一身冷汗:“太恐怖了,不过真挺吸引人的。史蒂芬·金不愧为一位伟大的讲故事大师。我猜测不出他是如何让读者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恐怖情绪的,也不知道他的故事中的刺激都来源于何处。但在他的作品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路线,将灵魂与魔鬼做出了有效的区分。”
【关于影片】
《1408幻影凶间》中,约翰·库萨克饰演了一名专门为世界各地著名的鬼屋写小说的作家,他研究过形形色色的“未解之谜”,发现所谓神秘事实背后的真相其实并没有那么扑朔迷离。当然,他也有过一段凄惨的经历--以导演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的话说,迈克是一个因为遭受了失去女儿的痛苦而变得反复无常的受伤灵魂:“他迷失了自我,因为他太悲伤、太压抑、太沮丧了,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正在寻找着什么。”
在接到一张急得火烧火燎、用词却极度模糊的明信片后--里面的内容是在暗指躲藏在1408室门后的秘密,迈克决定将这个神秘事件写进自己新书的最后一章里。他登记入住到纽约的海豚酒店,并在那里见到了酒店的经理奥林先生,约翰·库萨克表示:“迈克将1408室的秘密归咎于奥林和他的员工精心策划的一部分,如果将真相写在小说里,这家酒店的入住率至少会降低一半。”不过很快,迈克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库萨克接着说:“当他住进去之后,酒店的地址竟然变成了加州,而一些奇怪的事也真的发生了。就好像这个房间具有了生命,活了过来,而且攻击性十足。”
导演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表示:“迈克在1408室的遭遇其实更像是一种自己的心魔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形式,他必须克服恐惧,才能战胜这些可怕的事情。” 塞缪尔·杰克逊在影片中饰演杰拉尔德·奥林,相对于迈克来说是比较次要的角色。约翰·库萨克说:“我很喜欢和杰克逊一起工作,也许你会觉得奥林这个角色很多人都能演,但试着想象一下,似乎也就只有杰克逊最合适--如果他告诉你不要进那个房间,你就不应该进去。”
塞缪尔·杰克逊对自己的角色的理解是:“奥林已经在这家酒店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理了,并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他试着不让客人住进1408室,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想处理随之而来的一片混乱和麻烦。自从他在酒店工作以后,已经经历过4起死亡事件了,而这些人死前,似乎都经历了恐怖的惊吓……这里,迈克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奥林没有必要借助1408室危言耸听,提高酒店的知名度。因为这个房间里真的发生过一些事情,只是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除了这两个角色外,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女性角色,由玛丽·麦克马考(Mary McCormack)饰演,在影片中是迈克·安瑟林那冷淡的妻子莉莉。麦克马考似乎是所有演员中惟一对米凯尔·哈佛斯特朗姆以前的作品不熟悉的人,但是她的嫂子却是这位瑞典导演的好友,麦克马考笑着说:“就因为我说没看过哈佛斯特朗姆的片子,还惹得嫂子对我大吼大叫呢。既然我的家人、朋友和在洛杉矶的同事都不住地夸他,接下这个角色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麦克马考却表示,自己对史蒂芬·金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他的故事总能调动你的情绪,这才是最恐怖的。”说到迈克和莉莉之间复杂的关系,麦克马考则认为:“影片会以倒叙的方式让你看到他们以前关系好的时候的样子,但是自从女儿死后,他们就再也没办法恢复到以前的模样了。他们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不联系了,但我觉得他们仍然爱着彼此,只是陷入了一种情感交流上的僵局--他们不想谈论女儿,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无尽的哀伤淹没,可是除了女儿,他们又没有别的好谈论的


 在线咨询
在线咨询